《突圍》 下 第十七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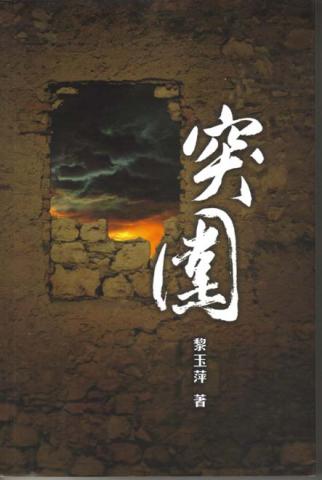
第十七章
草籽半岁了,他长得圆头大眼胖乎乎的,见人就笑,很喜欢蹬手蹬脚,煞是招人喜爱。每晚饭后,唐唯楠都抱他到河里玩水,玩一阵便抱他上岸。岸上总有几个十来岁的小女孩等着,不用他招呼就主动过来,帮他抱草籽回家。每每见到那些女孩抱着草籽,笑着玩着走在斜阳下,他心中无限感慨:“人啊人,为何就不能和睦共处,非要把自己变成野兽,斗个你死我活不可呢?”
小军和唐唯楠的感情日益深厚。天气稍热后,两人每晚都一起泡进河水里。今天,小军来得很晚,到了河边,他不像往日那样迫不及待地剥光衣服跳进河里,而是气鼓鼓地坐在岸边。
“怎么啦,病了?”唐唯楠问他。
小军摇摇头不说话。
“叫爸爸打屁股了?”
“不,他不打我的,只打我妈。”
“还在打吗?”
“停了,不过,我妈被他打得头上起了个包。”他捡起一颗石头恨恨地扔进水里:“我恨死他了,家里就他不讲理,横行霸道。等我长大一定收拾他。”
“怎么个收拾法?”
“揍他,也叫他尝尝挨揍的滋味。”
“你揍他,不就跟他揍你妈一样了?他之所以打你妈,只因为他气力大。”
“不一样,他是欺负我妈,我打他是替我妈出气。我是正的。”
“嗯,叔叔看到一些不公正,有时也会这样想。可打人只能把对方打痛而已,他并不知道错在哪里,既然不明白,甚至他认为自己根本就是对的,那么他必定再犯。那你是不是不停地打下去呢?”
“那怎么办?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横下去?”
“小军,打,确实很痛快,但用打的方法解决问题,我看不好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老打你妈吗?”
“他老说:女人是贱货,不打会成野马。吃饭时他们吵嘴,妈说他不讲理,还当什么支书呢,他就动手了。平常都这样,理亏就打人,真讨厌。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爸,和你差远了。”
“那你长大了,千万别学你爸爸。小军,有好多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,得慢慢来。比方说男人打女人,村里,哪个男人不打女人的?知道为什么吗?因为祖祖辈辈都这么打下来的,日积月累,错误的东西变成了正确,你不打才是错,是熊包。要他们不打女人,首先要让他们明白,打女人不对。男人强壮,女人柔弱。男人用天赋的强壮去欺负柔弱,这不叫英雄而叫可耻。有种的男人,该去拼比自己强壮的大傢伙。”
“他们不会听,没用的。”
“对呀,是很艰难的。所以我说一天两天解决不了。解决这些问题,不但需要力量,还需要知识和勇气。”
“知识?勇气?”
“嗯。人和动物不一样。人有嘴巴,会讲道理。你的道理从那里来?就从知识上来。从前,叔叔认识一位阿姨,她看很多书,懂很多道理,很多很复杂的问题,她都看得通,想得透。”
“她比你还厉害?”
“是。认识她以后,我才明白读书的重要。小时候我不爱读书,到现在,很多问题我都不会想。碰到困难想不通的感觉,就像头一次下水的人,前进不敢,后退不得,只知道心慌。”
“叔叔,以后我爸再打我妈,我该怎么办?”
“保护妈妈,叫他停手。”
“他不听呢?他力气比我大呢。”
“勇气。鼓起勇气和他理论,讲道理。告诉他女人是人不是牲口,男人欺负女人可耻。你平时有空就想好,准备随时跟他讲理。”
“嗯,我明白了。”
“明白就好,天快黑透了,还游不游?”
“游,游到对岸去。”小军说完,脱光衣服“咚”地跳进河里。
晚霞退尽,暮色沉沉。灰蓝向黑的天空,正慢慢收拢起散落在人间的色彩,大地随之煳成一片,只有四面的山岭如锯,不知高低地向高高在上的天排列锯齿。清明的圆月冒出山后,像被锯子锯掉一块。河面宽越百米,中间有一道暗流,倘在阳光下,那暗流似长带,清晰地蠕在河中。此刻,月色下,它正闪着凌乱细碎的诡异波光。
小军展开双臂来回游泳,唐唯楠在距他一臂的下游,护着他慢慢泅着。芬芳清凉的河水,透过每一寸肌肤每一个毛孔渗进心的深处,渐渐地,他觉得心灵肺腑,九曲回肠像被淘洗过一样干净。涤去污浊的身体异常轻盈舒畅,似乎,只要加速,再加速,人,就一定能在水中飞起来。
秋收之前,友姐的父亲专程登门回访。中午时分,他刚踏进袁家,上山打柴的唐唯楠也迈进家门。大家兴奋而客气地寒暄起来。来客把提来的篮子交给主家,并再三声明就几根番薯,不是精贵货。宗婶和阿草煮饭,三个男人让座递烟,客套一轮后坐下喝茶。唐唯楠抱着儿子,和两位老者坐成品字形。
“这小娃真趣致,我记得是立春落的草。”
“是的,你记性真好。”阿草听到客人夸讚自己的儿子,回头向这边甜甜一笑回道。
“会说话了没?”
“还没,只会咿呀乱叫。”
“年初你到我家,转眼快一年啦,日子真快。”友姐父亲对宗叔说。
“是。你一切还好吧?” 袁宗答道。
“马马虎虎吧,你们呢?”
“老样子。不过不瞒你说,自从阿鸣来了,我们,嘻嘻,算有个奔头。真要谢谢你们啊。”
“别客气。我一路走来看着,估计这趟晚稻收成一定不错。”
“对,是会很好,你们那边呢?”
“也八九不离十,差不多。哎,不过好也没用,收多收少都是白费,我们只赚个死做白活。”
“嗯,是这样。”
说到这里,两人目光相碰,两双眼睛彷佛是四个能快速吸纳和处理对方讯息的精密仪器,所有讯息在一瞬间都交换完毕,再也无需多说。庄稼对于他们,好比彼此都养了一个半残废的亲生仔,因为是唯一的儿子,明知不能指望又不得不仍怀希望一样,不能不说起他,但说了比不说更令人难堪。更糟糕的是,这特殊的废儿会下金蛋,不幸招来了一帮凶巴巴的强盗恶棍,逼令他们像伺候皇帝一样伺候自己的儿子,然后全部抢走他生下的金蛋,还立下诸多规矩,不许埋怨半句,甚至连不满、悲伤、绝望、无奈、愤怒的眼神都不能有。两老农都无可奈何地四目朝天,大概他们希冀通过仰视,让冒上来的种种难耐都落到心底深处,那不肖子的靠山凶着呢,会杀人的,绝不能让眼睛洩露心里的秘密。于是大家日复一日,罗织深如沟壑的皱纹堆满眼眶,且学会了随时排列出让人释疑的纹路来。
活着,总比死去好。
“农人天天面对土地却厌恶土地,不谈耕作、收穫和庄稼,圈里没有猪牛羊,园中没有鸡鹅鸭,犁耙箩筐都是公家的。这农人,就像一个憎恨韬略战术,无视胜负成败的将军,兼且营里无一兵一卒,手上无一枪一炮,却要被元帅逼着日夜作战,还要许胜不许败。荒谬吗?”唐唯楠深深替他们难受。
大家沉默良久,袁宗忽然醒悟:“嘿,我带你看看我的新房子。”
来客也如梦方醒:“好好好,进来时我就想好好看看,坐下竟忘个干净。”
袁宗领着客人围着房子兜圈。他从採石,挖地基,砌墙,开窗户,上主樑到铺瓦、抹泥浆如数家珍一一道来。说到最后,他一个劲地可惜人家住的太远,没法子帮他盖一间,那神态,好像自己独佔着好地方却忘记了老朋友那样不够意思。
唐唯楠抱着儿子,礼节性地一直陪着他们。吃饭时,他才开腔问友姐的情况,知道友姐的丈夫仍然下放,而友姐常常写信或者托人回娘家打探消息。他明白友姐的用意,他的情况友姐知道了,就等于母亲知道了。他想:“两年了,我连一封信都不敢发出去。孙子出生,妈已经当奶奶了,也不敢向人声张更不敢来看看,这是什么样的折磨?”
吃过饭,友姐的父亲要走了,宗婶把他的小篮子还给他。他看见里面放满了东西便一意推辞。这边坚持要送,那边固执要推,双方推来让去,都像家境富裕得不行,多一点东西都搁不下了似的。来客最终不敌这边人多势众,满委屈地提着篮子谢了又谢,回家去了。
晚上,唐唯楠辗转反侧难以入梦。阿草知道他是思念母亲的缘故,便问这问那诱他回忆过往的片段,引他吐出心中的积垒。
早晨,唐唯楠又踏上卖柴的山路。深秋的晨阳带着金色融进山岚,满山黄叶在金色的雾霭中微微颤动着,几分飘拂,几分迷离。田里的稻谷沉甸甸金灿灿,在晨风里沙沙作响。在山道上急行的他,直觉得自己掉进了金光灿烂的世界,活在一个金光灿烂的年代。他有力的脚步敲击着这沉静虚幻的世界。一只田鼠惊惧于这脚步,扭动肥胖的身体惊惶逃窜,躲藏。
快到捕鼠时节了。唐唯楠想起家乡那边吃田鼠的风俗,每年秋收后,大家就三五成群下田捕鼠,最常用的方法是烟熏。多的时候,一次能捕到十来斤。“哎,四只脚的田鼠好捕,两只脚,甚至没有脚的田鼠谁可以对付呢?”他想。如今,稻谷之于农人,关系好比乳娘和她怀里的孩子,尽管她殚精竭力地喂养,到头来这乳子与她全无关系。有奶便是娘的俗话还有一点人情味,毕竟他还认施乳者为娘。但对当今疯狂掠夺民众的强权者来说,乳母不是娘,更不是人。乳娘只是乳汁的载体,跟一只箱子一个木桶无什么区别。冷血乳子,只知道紧捏着乳母的乳房鲸吞海吸。天下乳母有的,只是敞开襟怀奉献奶水的责任,除此之外,她们一无所有。”他觉得好像有点不妥当,再仔细想想:“对了,可恶的不是这乳子,而是乳子的亲爹娘——有权掠尽稻谷的那伙强盗。”
眼前的金色是那样虚妄,那样炫目,有多少罪恶,在这迷幻的色彩下发生?金色,本该带着暖意,而此刻,山风吹来,唐唯楠只感到透骨寒冷:“金色是假的,稻谷也是假的,只有寒冷是真的,饥饿是真的,山边的荒塚是真的。”他从衣襟下摸出一块还有暖气的番薯,“还好,岳母给我的番薯也是真的。”
今天的柴卖给一个老头。这老头大概是个了得的官,他只向门卫打了个招呼,迳自让唐唯楠挑柴进厂,直奔宿舍,付钱后立刻亲自领他出厂。
“老同志,我认路的,你不用多跑一趟了。”唐唯楠说。
“不行,厂里规定不许外人进来。没我领着,你有麻烦。”
唐唯楠只好跟他循原路退回。
工厂依山而建,主干道是水泥路,路两旁只是看到宿舍、食堂、娱乐室、球场等等设施,但看不见厂房。路过食堂,空气中飘满了食堂特有的香味,跟部队食堂的味道一模一样,唐唯楠不由自主地深深吸了几口气。篮球场上正在比赛,他像老烟鬼犯起烟瘾一样,心痒手痒。他最喜欢打篮球,在部队时是个了不起的中锋,每次比赛一定少不了他。球,磁铁一样吸引他的目光,他藉故蹲下,慢腾腾地系鞋带。
老者在一旁催他:“好了没?快点快点。”
唐唯楠不经意地扫了一眼身边堆着的金属废料:“咦?这些零件怎么那样熟悉?枪,没错,这都是枪的零件!哦,原来这不是什么民用机械厂,而是一家兵工厂。”他抬头四看。
“小伙子,东看西看,没见识过吧?”
“是。真没见识过,很新鲜。工厂好大。”
“还用说,两千多人嘞。”
“生产任务足不足?”
“足,常常要加班呢,好多年没正经轮休过了。嘿,你这卖柴的好像见过点世面,懂得把柴挑到这里来卖,还会问生产任务足不足,哪来的?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。”
“过奖了。我确实不是本地人,不怕你笑话,没本事,只好到这里落户。这里的人很淳朴,只敢把柴挑到墟上卖。我也是没办法,家里有老有小,就靠我一个主劳力了,不碰碰运气不行。亏得有你们一直关照,我才有这个胆量。谢谢你,谢谢你们!大门在那边,你留步,看我跑过去得了。”说完跑了起来。他一溜嘴不停地说,无非是怕再遭盘问。
唐唯楠出了厂门拐上山路,工厂便隐蔽于万绿丛中。他想:“兵工厂兵工厂,在这山旮旯不显山不露水的地方,竟藏着一家两千多人的兵器厂,怪不得防范森严。省级头衔的南山製药厂,顶了不起才八百来人,还一天到晚任务不足停工停产,而他们两千人还要常常加班,可见这个社会,杀人的枪比救人的药更重要!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