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突围》 下 第十二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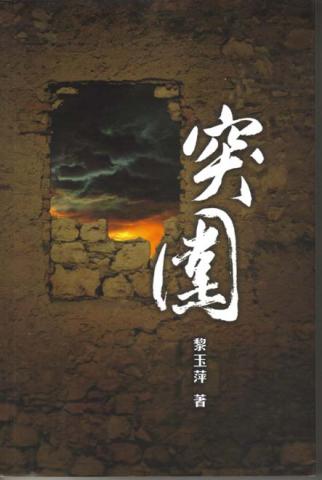
第十二章
炎炎夏日,最惬意的地方莫过于河边。每天傍晚,村里的男孩子都会剥光衣服跳进水里,狗仔式,自由式,又是比赛又是打水仗,“噼里啪啦”搅起一河灿金。唐唯楠有时和他们玩在一起,有时教他们游泳,有时则静静地坐在河边,看他们嬉戏。金色的晚霞,祥和的流水,真实的笑容,纯洁的心灵。多么美好的世界。
这天,小军双臂搂住他的脖子:“叔叔,驮我过河。”
“你已经学会了,自己游,我带你。”
“好。”两人才游出几米,忽然一个小女孩气喘吁吁跑到河边大叫:“鸣叔,快回家,草姐在吵架,快打起来了。我从没见过她这么凶的。”
唐唯楠立刻上岸:“小军,帮我拿东西。”他顾不上换下湿裤,抓起长裤囫囵穿上就往家里跑,老远就听到吵架声,“她和谁吵架?好像是坤嫂的声音。”
袁宗夫妇嘴上劝不动就动手推女儿回家,但阿草死命抵着誓不后退。老两口怕强硬拖拉会伤及胎儿,正当无奈之际见女婿回来便说:“阿鸣,快叫她回家。”
唐唯楠走过去挡在阿草的面前:“别吵了,回家去。”
“不回,就不回。”
见阿草不从,唐唯楠一哈腰一把抱起阿草,用脚踢开院门,“蹬蹬蹬”直奔回房间,把她放在床上。阿草还要扑出去,但推不开挡在门前铁塔似的丈夫,只好气呼呼一屁股坐回床上,嘴里仍然不干不净地骂。
宗婶端来一碗水,“你呀,算了,和这种人有什么好吵的?谁不知道她是什么货色,又刻薄又小气。”她把碗交给女婿:“你好好整治她,我还有事做。”
唐唯楠把水送到阿草嘴边:“你这么激动,有没想过他。万一把他提前吵出来谁吃亏?”见阿草停住嘴了,他又说:“先喝口水消消气,再慢慢告诉我发生什么事。”
阿草喝了半碗水,用手背擦着嘴巴恨恨地说:“她和我一组,向来喜欢向我使黑脸。我复工后,她天天嘴巴都不干净,句句话都冲着我。我一直忍她,可她越发轻狂,不知高低。哼,老虎不发威,她把我当病猫。”
“但你想想,她天天挑衅无非是想惹你生气,你越生气她越来劲,这不正好中她圈套了?”他指指阿草的肚子说:“你生气,对他不好咧。”
“可我实在气死了,你不知道她说的话有多难听。”
“她说什么随她说去,你不理她,她就没办法了。”
“不行,我不能随她那张臭嘴乱说我们。她不但说我,还说你。你听了也会气的。”
“她说我了吗?我可没得罪她。”
“没得罪她也照样说。她骂你是个野男人,还有……”阿草没说下去。
唐唯楠蹲到阿草面前,“就为这生气?”
“你不气吗?我们可是明媒正娶的。”
“我认为她说得没错,明媒正娶我也是个野男人。你怎么不这样回她?”他捏着鼻子吊起嗓子,学着女人吵架的样子低声说:“是,我就是喜欢够野,够壮,够劲道的野男人,怎么样,你没试过?呸!”
一句话逗得阿草哭笑不得,捏起拳头砸他。
“好啦,笑过就没事了。别往心里去。知道她是什么人,以后让让她就是,犯不着拿自己身体冒险。”
阿草不再说话。
唐唯楠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,但没几天,阿草和坤嫂再次大吵起来。唐唯楠不得不搬出诸如:做人要宽宏大量,少去计较得失,不好为了争一口气就坏了自己身体等等大道理去说服阿草。谁知阿草这趟不但不买账还反击他:“你就会说我,你自己呢?你不是也因为不愿意吃冤枉才这样的?现在结了婚,眼看要做爸爸,你不是还念念不忘要出去报仇?你叫我放下,那好,你也放下,从今往后不再提那个走字。”阿草忽然找到一个永远留住他的绝好理由,于是她振振有词,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说他:“我们都一起宽宏大量,否则,你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,自私鬼。我吃冤枉你叫我忍,你吃冤枉就半点不能忍。事情老早过去了,你还死死惦念着,你有没想过你的爸爸妈妈,老婆孩子?即使你自己不要命,难道,这么多人加起来,也抵不上你心里头的东西?我不想让你走,不能看着人家害你。呜……”阿草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唐唯楠似被一轮乱枪扫中,颓然倒在床上。
阿草哭过一阵,抹干眼泪伏在他身上,用双臂搂他的腰,却发现自己犹如抱住一截没有生命的木头。她看看丈夫,只见他脸皮僵硬,双目失神,直勾勾地盯着屋顶。敢情刚才的话太冲气着他了,她慌了,连忙伸手推他:“你别这样吓人,我说错了。”见他还是没反应,阿草更慌神了:“你说话应我呀,别这样,我以后不和人吵架了。鸣哥,鸣哥,你相信我,再不行打我几下,男人打女人很平常。求你别这样。”
她哀求了好一阵子,才见丈夫的眼珠“咕噜”一转,幽幽说道:“我能动手打女人,就不会到这里来。”
他的声音好像是从屋顶飘下来,阿草一阵心寒。
“再说,你的话未必全错。”阿草心头又掠过一丝希望,却见他直起身体,木然出门。
“你要去哪里?”
“我很乱,出去走走。”那声音仍旧虚虚空空。阿草看着他高大的背影转出屋外,悔恨自己抓错了救命稻草。
向晚的天空,蓝盈盈没有一丝云彩。唐唯楠自觉身体如抽去了所有桥墩的断桥,正沉沉下坠。一阵风吹来,桥面忽忽悠悠,飘飘荡荡,飘过山,荡过河,落在一片凄清草地上。心却如火中之栗,在剧烈地膨胀炸裂。父母亲情,这最不能触及的伤痛,叫阿草锋利的语剑猛然割开,迫使他不得不直视这骇人的伤口,清醒地去抵受裂骨之痛:“如果说,之前的事都来得太突然,一切都由不得我,那么现在呢?今天,我可以选择。选择彻底抛弃唐唯楠,只做余鸣。但像一只缩头乌龟,一只见不得光明的老鼠那样苟且偷生,我做得到吗?可为了关爱我的人,又有什么不可?我是否真的太自私?只顾自己的感受,不顾一切地坚持而令双亲受罪,让亲人忧心?一年前,我执着于一己之情感,使微霞无辜殒命;一年后,我又执着于逝去的历史,不惜伤害阿草和即将降生的孩子。一切的错都在我,阿草说得对,我是个只顾自己,罔顾亲情的自私鬼!我应该死。唯有一死,方可向亲人谢罪!”
“夜,请将我撕开,将我吞没,将我搅碎,将我融化。我没脸想起父母,再见阿草,更没脸面对晚霞!后天,就是微霞的忌日。微霞,告诉我,仰药的一刻,你可曾想到你的爸爸?想到我?你凭什么可以如此决绝?”他想起余微霞的照片和那双小辫子,想起辫子上的红蝴蝶,还有照片背后的唇印和泪印。“有的,有的。她的心里一定有我。然而,她仍然作了抉择。微霞,到底是什么东西,比自己的生命和爱人更重要?来到今天,我应该坚持?还是放弃?”
一个灵魂,在摇摇晃晃的断桥面上徘徊,在风中挣扎。桥的一端是莽莽森林,另一端是无底深渊。
连日来,阿草看着丈夫寡言少语不怒不笑,终日拧紧眉头不做一事,她懊悔不已。他是个爱干净的人,再忙也不让脸上长出胡子青苔,这些日子,他不但对任何人不理不睬,还任由自己的脸皮长成一片荆棘地。
宗婶见此状况甚为忧心,多次问阿草到底发生什么事,阿草不敢向母亲明言,只推说他气恼自己和坤嫂吵架。宗婶恨不得给阿草一个大耳刮,她斥责女儿:“你真不识好歹,嫁给这样的男人你还逆他。拿镜子照照你自己的样子,不知足。他这么个人品,能吃得下自家老婆这么烂泼,像只癫鸡一样的?难怪他生气。”
傍晚收工,阿草见唐唯楠走向晚霞,她决计要跟着他。
“回家吧,别跟着我。我没事的。”
“是我弄成你这样的,你让我和你在一起,起码,你说话也有人听着。”
见阿草一意坚持,他只好由她。来到村外的小树林,阿草见他坐下就走到他身旁,双手合十向着晚霞跪下。
他见状忙拉起她:“你要干什么?”
“我没用,只好求她来帮帮你。鸣哥,你这样子,我好害怕。”
唐唯楠拉起她,没说话,只用双手托住自己的头。
“鸣哥,和我说说她是个什么人。我猜,她的名字有一个霞字,一定长得很好看。是吗?”阿草坐在他身边,轻轻地推他。
唐唯楠抬起头,右掌罩在鼻子下,眼睛看着远方好一阵才说:“是的,她叫微霞。她有一头乌黑的头发,一双明亮的大眼睛,一对很深的酒窝。她善良温柔,很有见地。虽然我们只相处了几个月,很短很短的时间,可她给了我很多很多。白天,她是我的阳光!夜里,她是我的星光!我的灯塔!”
“那为什么要分开呢?”
“她走了。拒绝迫害,永远地走了。”
阿草听到他的声音在颤抖。
“鸣哥,她有你这样不要命地死死念着,换了我,我也愿意。”
唐唯楠侧过头来:“吃醋了?”见阿草摇摇头又点点头,他不解其意:“什么意思?”
“按理,她已经不在了,我不应该吃醋,可她永远都在你的心里,又吃了。不过,我是个啥也不懂的丑山妹,能跟你在一起,不管多少日子,我都应该心足。那天,我说了不该说的话,我不是故意捅你的。你相信我,我只想留住你。”
“这几天来,我一直在想你的话。你说的也有对的,我是很自私,但是我又觉得我应该坚持。想来想去,还是没想出个子丑寅卯。”
“要么先放一放,别往死里想。或者有一天会忽然想通的。鸣哥,从今往后,我不再和人吵架了。”
“嗯。我小时候妈就教我:两斗结仇,两和结友。和人相处要与人为善,肚量要宽广,心胸要阔大。吵架只会越吵越糟糕。”
“你妈就是我妈。妈今年几岁了?你长得像妈还是像爸?”
“她今年刚好五十岁。大家都说我长得像妈。本来想要好好孝敬她,可万万没想到……”说到这里,唐唯楠不禁失声痛哭:“对我的父母,我的亲人,我罪孽深重不可饶恕啊。”
阿草站起来,把他的头抱在怀里,拍着,陪他垂泪。
“阿草,我们没结婚证也是好的,将来,不管我出什么事,我们不是合法夫妻,你把责任都往我身上推。”
“不,我们是夫妻,一条心的。”
“不,你记住我的话。即使一条心,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。你还要孝敬长辈,抚养教育孩子。这个责任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阿草点头,泪如雨下。
